沈从文的名言
沈从文的名言
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溪面各处飞着红蜻蜓。天上已起了云,热风把两山竹篁吹得声音极大,看样子到晚上必落大雨。
我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睛这样冷,有个人的心会结成冰。 我看过多地方云走过多地方桥喝过多地方酒只爱过正当好年华女子
热情既使人疯狂糊涂,也使人明澈深思。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黒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切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
有些路看起来很近走去却很远的,缺少耐心永远走不到头。
照规矩,一到家里就会嗅到锅中所焖瓜菜的味道,且可见到翠翠安排晚饭在灯光下跑来跑去的影子。
征服自己的一切弱点,正是一个人伟大的起始。
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
人生实在是一本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
宁可在法度外灭亡,不在法度中生存。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第二篇:沈从文和他的《渔》
人事中杂糅的神性与魔性
——沈从文和他的《渔》
央视国际 (20xx年01月26日 11:20)
作者: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县人,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后来到北京寻找新的人生,并开始文学创作,从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弊病,“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
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讲解:商金林
商金林,男,江苏省靖江市人,19xx年出生,19xx年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叶圣陶年谱》、《闻一多研究述评》、《叶圣陶传论》、《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
《感觉日本》、《求真集》等。
拓展阅读:
《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沈从文印象》巴金等著,学林出版社
今年12月28日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沈从文,9月17——20日在他的家乡湘西凤凰县举办了“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这个论坛是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湖南吉首大学以及凤凰县县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我参加这个“论坛”,又在湘西走了沈从文当年走过的一些地方,获
益匪浅,先就“湘西与沈从文”这个议题,谈两点感触:
湘西和沈从文
1,我们对湘西还比较陌生,需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湘西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族、土家族、苗族、回族、壮族等41个民族。湘西是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方。自然风光雄浑壮阔,苍秀奇绝。凤凰县城坐落在湘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位于沅水上游的沱江之畔,襟山带水,小巧玲珑。是个苗汉杂处的小小山城。窄窄的街巷,清一色的石板路。房屋大都是砖木结构,青瓦玄墙,还有那相传是由巢居演变而来的吊脚楼,显得极为古朴。凤凰县城有坚固的石头城门。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一类作品里可以知道,这城门维护着的是一方神秘的天地,在这里演出过无数悲壮凄楚的故事。19xx年前后,凤凰城里的居民不过五千,而正规兵士却有七千。周围山山岭岭的历史,宗教的种种潜流都汇拢到这个小小的山城。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侠义与巫术、强暴与善良、野性与剽悍、封闭与愚昧使这个山城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浓郁的血腥味。湘西民族性中确有凶狠,野蛮,好斗的一面。另一方面,这里的民风又极淳朴,人们正直,忠诚,爱美,认真,特别“圣洁”。不会说谎,不会作伪,沈
从文在很多作品中也写到这些,例如短篇《巧秀和冬生》。
短篇里的巧秀家住在溪口,妈妈23岁就守了寡,那时巧秀还不到两岁。巧秀妈年轻,跟黄罗寨的打虎匠相爱,被族里人发现了,族里人觉得受到了侮辱,要惩罚打虎匠。所谓惩罚,原本是雷声大雨点小,打一打就算了,但是族长不同意,一定要严惩。巧秀妈未出嫁时,族长曾经想要她做儿媳,巧秀妈不同意,因为族长的儿子是跛子。后来族长又想调戏她,被巧秀妈骂了一顿。为了泄私愤,族长让人当着巧秀妈的面,把打虎匠的双脚捶断。打虎匠被抬回黄罗寨时,巧秀妈跟着要去黄罗寨伺候他,族长大为震怒。为了维护本族的名誉,决定把巧秀妈“沉潭”(沈从文《月下小景——新十日谈之序曲》中称这是“魔鬼的习俗”,“古代的规矩”),免得招惹黄罗寨人笑话,看不起溪口人。他们把巧秀妈的衣服脱光,绑起来,脖子上挂上个石磨,推到船上。船向长潭划去,巧秀妈一声不吭。船划到了最深的地方,一位年长的族人问她:“有什么话嘱咐?”巧秀妈想了想,低声说:“三表哥,做点好事,不要把我的女儿掐死喔,那是人家的香火!长大了,不要报仇,就够了!”话刚说完,冷不防一下子就被掀下水了。你们看巧秀妈多么纯朴,对她死去的丈夫,对打虎匠,对整个族里的人没有一多怨言。沈从文很多作品里都写到这样纯朴的人,有的人要挨枪毙了,临死前还给家人讲:我还欠别人的桐油,一定要还。了解当地人性纯朴的一面,才能更好地把握沈从文的作品。现在的凤凰县民风也还比较淳朴,漫步在凤凰街头,可以看到商贩和店主不会漫天要价,买主也不好意思讨价还价。据当地警察说,凤凰城社会风气好,当地人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发生的刑
事案件大多是外地人干的。在沈从文生活的青少年时代,这里的民风更淳朴。 人们今天谈论起沈从文小说中描写的湘西世界,往往说是浪漫的传奇、童话故事,好象纯系想象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边城》(生活书店,19xx年10月初版),有人说《边城》所写的是“乌托邦”,“诺亚方舟”,“君子国”,是“世外桃源”。说《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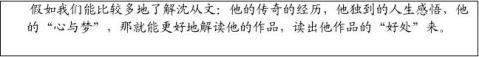
城》小说中“人与环境都是作者编造出来的”,“是作者主观头脑的产物”,话说得很绝对。沈从文说他小说纪录的人事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活动。(沈从文《短篇小说》,《全集》第十六卷)既然写“社会现象”,当然就有一定的真实性,甚至会有蓝本,有原形。例如《边城》中的“茶峒”就确有其地,现隶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桃垣县管辖,是一个乡政府所在的小镇,当地人叫“茶洞”。“茶洞”是苗语的音读,意思是“山边的一块平地”。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巴蜀边隅万年古镇,位于湘、黔、渝三省交界处。“茶洞”依山凭水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蜿蜒;临水的一面,荡漾着渡船。这条河叫酉水。河这边是湖南,过了河就是四川(现属重庆),贵州(两省的山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地人戏称为“一脚踏三省”。沈从文就是以这里为蓝本创作了不朽名作《边城》,蜚声中外。相传翠翠住的楼房还在,沈从文写作的小楼还在,码头还是当年的码头,过渡的渡船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式。“茶洞”风情依旧,似乎还定格在七十年以前,停留在沈从文写《边城》的那个年代,让人们来回味。假如我们对曾经养育过沈从文的湘西这片大地有较深入地了解,我们也许会更清晰地看到沈从文创作源泉——是湘西这个“野蛮而神秘;有奇花异草与野人神话的地方”孕育了沈从文。虽说沈从文的作品中也交织着“梦的现象”,这“梦的现象”虽说是“以新的形,尤其以新的色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蕴积和躁动的依然是湘西的“魂灵”,烙下的依然是湘西社会的“胎记”,就连沈从文自己的人生理念,也都是湘西大地哺育出来
的。
例如沈从文爱“水”,引水为知己。他在《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文集》第11卷)和《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xx年3月——7月)中,一味地赞美水对他的帮助、
启迪、教育、陶冶和鼓励:
到15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分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水发生关系。??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识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面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于未来生活有何安
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
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学会思索,认识美,水对于我有
极大关系。
水教给我粘合卑微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
普通个人的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生活中,会时常听到有人会骂“水”,如穷山恶水、污泥浊水、拖泥带水、水性杨花、水货,等等。但这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水”,大自然的“水”。作为真实意义上的“水”和大自然的“水”是一直为人们赞美的。水有“智”、“礼”、“勇”、“德”等儒家所崇尚的伦理品德。孔子说: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关于“智者乐
水”,汉初,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有一段解释:
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似有智者;重而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至远,似有德者。天地以成,万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此智者所于水也。 沈从文对“水”的认识和体悟,似乎比韩婴的解释还要丰富和深刻一些。他在杂文《沉默》(《沈从文全集》第十四卷)中说“沉默”如“水”。“水”看似“沉默”,但滴水可以穿石,遇风可以扬波;把温度升高,可以化为蒸气;温度降低,可以变成坚冰;自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何处何物里面,无不有水的存在。水能深入一切而不变质,而水质又最坚,具有一种不怕任何阻碍而非达到一定的目的不可的特性。譬如江河,它一定要向东流,非达到入海的目的不可。为要达到入海的目的,它不避一切艰难,不畏任何险阻,也不择任何途径,透过岩石,渗过沙泥,走过溪流,或回还曲折,或奔放畅流,是这种韧性的作风,使水有着坚定的向东流的信念。沈从文把“水”的“流”向视为“人”的“行”的真谛。他说“水”给了“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培养了我孤独的心情”,“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他在《我的写作和
水的关系》中说:
(19xx年夏天)我离开了那条河流(湘西辰河),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是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
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的人的言语太多了。
小说中的故事,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文字中的忧郁气氛,文字的风格,都源自湘西辰河。都来自“水”上,是“水”营造了沈从文,营造了他的小说。沈从文的这些描述,寓言极其深刻。湘西群山环抱,奇峰挺秀,风景优美。另一个方面,湘西地处湘黔边境,交通闭塞,出门靠的是“河”,湘西的“河”,其实就是我们脚下的“路”。在湘西“水”显得格外重要。沈从文从“水”中学到的不仅仅是做人必须要有的“一种水的素质”:“孤独一点”、自然一点、随意一点、通脱一点;还从“水”上走出了凤凰城,认识外部的世界,看到了各地的“乡村人事”,“人民的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我们如有机会到湘西看看,就会理解沈从文对“水”的感情,对沈从文的作品与湘西大地
的关系也会有更深刻的感悟,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欣赏会有多方面的启迪。
2, 我们对沈从文还知之甚少
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指家里人)不了解他,研究者也不了他,他的朋友也不了解他。这话大概也是有感而发的。我们对一个作家了解得太少,是会影响到对他作品的阅读的。郁达夫曾经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话有点太绝对了,但它突出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强调要认识作家这个“人”。沈从文出身于“两代军门之家”。祖父叫沈洪富,曾经当过贵州的提督(最高军事长官)。父亲沈宗嗣也曾当过军官,19xx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他镇守大沽炮台失守了,丢官后回家乡行医。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沈从文家中兄弟姐妹九人,沈从文在男孩中居第二,同胞弟妹全都叫他“二哥”。沈从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凤凰县城度过的,他的故居至今保存完好。读过沈从文自传的人都知道,沈从文自幼调皮,
用他自己的话说,叫“顽劣”,和他的一帮伙伴们爬树、打架斗殴、偷人家的萝卜水果吃,斗蟋蟀,以至上赌摊赌钱。沈从文的“顽劣”,大概是受了当时湘西社会的“野性”、“骠悍”、以及游侠精神影响所致。也正是因为沈从文从小“顽劣”,不受拘束,且日益放肆,逃学撒谎,使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非常灰心(父亲希望他当一个将军)。母亲也想不出处置他的好办法,便过早地让他进县预备兵的技术班,接受军训。时为19xx年,沈从文才14岁,刚刚小学毕业。所谓的预备兵技术训练,学的是翻筋斗,打藤牌,舞长矛,耍齐眉棍,19xx年正式参加部队(土著部队)。从19xx年到19xx年的五年间,沈从文在川、湘、鄂、黔四省边界部队里,经历了各种残酷的演绎。他所在的部队,杀人就数以万计。所谓清乡剿匪,实际上是依惯例杀人,拿血腥敲诈。沈从文也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例如19xx年冬,沈从文所在的部队,在鄂西来凤县遇到当地“神兵”的偷袭,仅仅一个夜晚,全部被砍尽杀绝。沈从文因身体瘦小,得以留守阮陵,侥幸留生。沈从文这些残酷的传奇的经历,使他过早地咀嚼到人生和社会的滋味。在那个年代,所谓前途,所谓命运,转瞬间就会一切成空。生命之途,有太多的偶然和意外,只有雄健的、顽强的抗争,珍惜生命,才能无怨无悔。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要压抑,不要浪费,甚至不要犹豫彷徨,要勇于面对自我,敢于实现自我,真实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就是在这样自然、残酷,然而又是最本质的教育中树立起来的。
他在19xx年写的《自我评述》(《光明日报》19xx年5月29日)中说:
小时因太顽劣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土著军队中当兵,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 荡了五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我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味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痛苦怕人生活(在《﹤从文自传﹥附记》中说“噩梦般恐怖黑暗的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一九二二年“五四”运动余波到达湘西,我受到新书报影响,苦苦思索了四天,决心要自己掌握命运,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从此就如我在《从文自传》
中所说,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习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从这篇自述中可以看出,五年的行伍生涯,对沈从文来说影响太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生活中充满疑问,都得我自己去寻找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而我所知道的又太少。”沈从文急于追求的不仅仅是“要自己掌握命运”,而是着眼于“这个社会必须重
新安排”的思考。
我有幸在沈从文先生晚年拜访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太美好了,那么渊博、慈祥、谦和。再回头看他青少年时代的照片就很有意思。美国学者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中刊登了二帧,一是沈从文小学时代的照片;一是19xx年上北京前在湖南保靖拍的照片。就照片说照片,第一帧可说是不驯服的顽童,第二帧可说是粗野蛮横的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烛虚?五》19xx年5月5日),就长相说,这话不假。这本书中还刊登了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照片,最早的一张是19xx年在青岛拍的。照片上的沈从文俊秀潇洒,笑得非常甜美(台湾《中央日报》19xx年6月9日的报道中说沈从文“面目姣好如女子”)。与19xx年在湖南保靖拍的照片相隔仅仅十年,但容貌焕然一新,几乎看不出有相似或相近的迹象,“变”得有点奇异。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从父亲希望“将军梦”里走出来,想升学读书,立志“从文”,从某
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浪子缩手皈心”(《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甚至可以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沈从文在“求学”“从文”这条道路上忍受的苦闷、经历的艰辛、付出的心血,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土著部队的文书、屠宰收税员,变成了大学教授、知名作家。这个过程、这个飞跃,决不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的套话所能概括的。从照片上的神情和气质所发生的“蜕变”看来,沈从文历经的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一直说他是“乡下人”、“乡巴佬”,他所说的“乡下人”、“乡巴佬”主要指的是他对“城市文明”的抗拒,他身上保留着湘西人正直、纯朴、无私、爱美的品格,以及他热爱湘西大地的情结,骨子里坚守着作为一个“乡下人”所特有的审美情操和道德理想。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沈从文的“蜕变”,使得他“脱胎换骨”,我以为很可能还是沈从文自己所说的——他“自己的心与梦”。这“心与梦”,是沈从文作品的底蕴,或者说是亮点,集中地表现为对于“人性”的思考,对于“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
式”的思考,对于“生命哲学”的思考。
表面上看,沈从文忌讳谈政治,忌讳谈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他在《从文小说习作
选?代序》中说: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故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
是什么意义。
19xx年5月,沈从文在吉首大学演讲时,有一位教师提问:“沈先生,你《边城》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沈从文听了这个提问,竟流露几分惶惑的神色,说:“不,不,我从来不懂得他们所说的那个‘主题思想’,我写作不兴那个,想写就写起来了,写到感觉应该停住也就停住了。”“想写就写起来了,写到感觉应该停住就停住了”这两句话很重要,可见沈从文的创作都是有感而发,不是抽象概念的演绎。沈从文到底“想写”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点狂妄想象”,是自己“生命中属于抑压的种种纤细感
觉和荒唐想象”(《水云》)。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说: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 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
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个人
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沈从文还说过:“发现美接近美不仅仅使人愉快,而且使人严肃,因为俨然与神对面!”(《看云录》)希望读者能“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于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在谈到《边城》到底可给读者一点什么时,沈从文说,如果读者不被一些说教者蒙住眼睛和凝固了兴味,那么:“你接近我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甚至与痛苦难堪,多少总得到一点点。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以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细细品味这些话,就能体会到沈从文特有的那种“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沈从文的作品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缺乏深度”,“没有深入到生活的底蕴”,是引人“向后看”。出现这些批评的原因,或许有文学论争的影响,有作家间的恩怨,但恐怕与没有好好地读沈从文作品不无关系,没能读出沈从文作品的好处来。
为此,沈从文颇有感叹,他说: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
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
我们忽略的是“蕴藏”在清新的故事背后的“热情”,以及“隐伏”在朴实的文字背后的“悲痛”。为什么会“忽略”这些,恐怕与我们不了解沈从文有关。诚如他的儿子虎
雏所说的:“我们不了解他”。
假如我们能比较多地了解沈从文:他的传奇的经历,他独到的人生感悟,他的“心与梦”,那就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读出他作品的“好处”来。19xx年,沈从文去世的消息传到瑞典,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在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中,称沈从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伟大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作品“是在寻求与全人类有关的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没有沈从文,世界就要贫乏
得多!”这话是值得揣摩的。
说起我们对沈从文知之甚少,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就是沈从文的学识和才华。沈从文只上过小学,他说:“我文化是最低级的”。但沈从文不仅小说、散文、诗歌写得好,评论也写得相当出色,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小说史,是地道的学者型作家。沈从文的书法好,字写得特别漂亮。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教员的书法作品选,汇集了许多北大知名学者的书法作品,有人评价说:沈尹默的字排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沈从文。沈从文的书法,尤其是草书,清新秀丽、遒劲潇洒。诗人荒芜称赞说:“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墨来。” 沈从文喜绘画。画家黄永玉介绍说:“从文表叔有时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他提到某些工艺品的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沈从文喜爱音乐,小时候学过吹号和击打锣鼓,后来会吹箫、弹琵琶、唱昆曲。他认为:音乐能拯救人们被毒害了的灵魂,能解除人的烦恼。他说,“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似的。”沈从文的作品写得很美,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动静协调的美,这与他的绘画和音乐的才华不是没有联系的。解放后,沈从文从事瓷器、丝绸、服饰等物质文化史研究,用他的话来说接触的是绫罗绸缎,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在物质文化史领域成就卓著。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源自他的书法、
绘画和音乐的才华。
总的说来,沈从文的艺术造诣高,涉及的领域宽,底蕴厚势,又特别勤奋,精进不懈,从而成就了他的事业。有人说沈从文是“天才”。沈从文说,“我是最不相信‘天才’的,学音乐或者什么别的也许有,搞文学的,不靠什么天才,至少我是毫无‘天才’,主要是耐心,改来改去,磨来磨去。”——这是他的经验。他从19xx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到19xx年才比较成熟,文字才比较通顺。现代作家中有的人“一鸣惊人”,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代表作,起点就是顶点。沈从文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走过
来的,值得钦敬。
关于《渔》

1,“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
下面就来谈谈《渔》,这个短篇写于19xx年,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写得相当好。小说写湘西华山寨乌鸡河两岸七月的某个夜里“捕鱼”的风俗。很久很久以前,乌鸡河左岸属于甘姓大族,右边属于吴姓小族。吴族因为族小,为生存竞争,子弟都强梁如虎如豹。甘家大族中出好女人,多富翁,族中读书识字者比持刀枪弄棒者为多。象世界任何种族一样,两族中在极远一个时期极小事情上结下了怨仇,直
到最近为止,机会一来即有斗争发生:
过去一时代,这仇视,传说竟到了这样子。两方约集了相等人数,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互相流血为
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在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于头上,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平常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般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方块,加油盐香料,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另一端,也正有人在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两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这事情到今日说来自
然是故事了。
相传在这地方过去两百年以前,甘吴两姓族人曾在乌鸡河荒滩上各聚集了五百余彪壮汉子大战过
一次,这一战的结果是双方同归于尽,无一男子生还。因为流血过多,所以这地两岸石块皆做褐色,仿佛为人血所渍而成。这事情也好象不尽属诸传说,因为岸上还有司官所刊石碑存在。这地方因为有这样故事,所以没有人家住,但又因为来去小船所必经,在数十年前就有了一个庙,有了庙则撑夜船过此地的人不至于心虚了。庙在岸旁山顶,住了一个老和尚,因为山也荒凉,到庙中去烧香的人似乎
也很少了。
因地方进步,这种野蛮的杀伐演变为“渔”,让那些感到蛮力无处可发泄的汉子有一个发泄的机会。七月某一天夜里子时,在乌鸡河的上游的滩口放药,药沉到水中,与水融化,顺流而下。河中鱼虾中了毒,昏头眼花浮于水面,乌鸡河两岸甘姓、吴姓两族的后人,打起起更鼓,携箩背刀,各人手持火把,跳到河里去,在月光下挥舞起祖辈流传下来的用于仇杀的锋利的大刀,撩砍水面为药所醉的大鱼和水蛇。“渔”是历史上甘姓、
吴姓两族仇杀这一野蛮习俗的变异。“渔”成了华山寨的狂欢节。
小说构思巧妙。负责乘船五里到上游放药的是吴姓孪生兄弟,这孪生兄弟“模样如一人,身边各佩有宝刀一口,这宝刀,本来是家传神物,当父亲落气时,在给兄弟此刀时,同时嘱咐了话一句,说:这刀应当流那曾经流过你祖父血的甘姓第七派属于朝字辈仇人的血。说了这话父亲即死去。然而到后这兄弟各处一访问,这朝字辈甘姓族人已无一存在,只闻有一女儿也早已在一次大水时为水冲去,这仇无从去报,刀也终于用来每年砍鱼或打猎时砍野猪这类事上去”。“时间已久,这事在这一对孪生兄弟身上自然也渐渐忘记。”乘船到上游放药,引起了吴姓兄弟对于吴姓、甘姓两族血仇的记忆。溯流而上,其实是追忆逝去的岁月,追忆吴甘两族人的恩恩怨怨。而上游五里处沉船放药的荒滩,相传就是“过去两百年以前”吴甘两姓族人血战的战场,荒滩、两岸褐色的石块,
石碑,古庙成了两百年前,那个野蛮黑暗年代里甘吴两姓族人仇杀的见证。
吴姓兄弟到了沉船放药的荒滩后,因为时间尚早,就上岸游玩,到山上去看庙,访和尚。这些看似很自然,很随意的闲笔,其实又都是沈从文独具匠心的设计。断黑之后的深夜,梦幻似的朦胧月光下的荒滩,乱石、河流、古庙、山峦,以及水边来来去去的流萤、荒滩上嚖嚖作声的蟋蟀,使人犹如回到了蛮荒时代,再现的仿佛是“过去两百年以前”的自然景观。而和尚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吴甘两姓族人那场“同归于尽”的仇杀中幸免者的后人。和尚泄漏甘姓朝字辈族还有人存在,而这个人可能就是谣传被大水冲走的那位女儿。她存在的迹象,就是弟弟在山庙前捡到女人留下来的一束野菊花。和尚和野菊花的出现把两百年前残酷的仇杀和现实联系起来,增加了那场“同归于尽”的仇杀的真实性,使这场仇杀成了有迹可循的历史,同时又渲染这场仇杀的残酷和荒诞。古
庙、和尚、木鱼、颂经,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对那场仇杀的忏悔。
吴姓孪生兄弟,模样如一人,但气质各异。虽说弟弟常常听从哥哥的决定,但两人的性情爱好则相反。哥哥强梁如虎如豹,勇武好战,上山的路上,拔刀顺手斫路旁的小
树,飒飒作响,一面挥刀一面对弟弟说:
爹爹过去时说的话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刀是为仇人的血而锋利的。只要我有一天遇到这仇人,我想这刀就会喝这人的血。不过我听人说,朝字辈烟火实在已绝了,我们的仇是报不成了。这刀真委屈
了,如今是这样用处,只有斫水中的鱼,山上的猪。
哥哥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要寻仇人报仇的事。在山上的庙前,哥哥又在月光下舞刀,“作刺劈种种优美姿势,他的心,只在刀风中来去,进退矫健不凡,这汉子可说是吴姓族最纯洁的男子了。”最后在河中勇敢如昔日战士,挥刀斫鱼杀蛇,以发泄大仇之恨。弟弟则富有诗人气质。在上山的路上,在月光下,弟弟爱听蟋蟀的歌吟,为忘了带
笛子而感到遗憾。明月清风使他情绪缥缈。在庙前捡到一束野菊花,就推断:
“这是女人遗下的东西”;
“这是甘姓族中顶美丽的女人”;
“莫非和尚藏——”(女人)
这句话没说完,自己忽然忍住了,“因为木鱼声转急,象念经到末一章了。”木鱼声让弟弟终止了和尚藏美女的猜想(沈从文对和尚似乎没有好感,在作品里写到和尚好酒色)。接下来,哥哥在月光下舞刀,弟弟则陷入这一束野菊花的遐想中:“他把那已经半憔悴了掷到石桌上的山桂野菊拾起,藏到麂皮抱肚中,??他这时只全不负责的想象这是一个女子所遗的花朵。照乌鸡河华山寨风俗,女人遗花被陌生男子拾起,这男子即可进一步与女人要好唱歌,把女人的心得到。这青年汉子,还不明白女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因为凡是女人声音颜色形体皆趋于柔软,一种好奇的欲望使他对女人有一种狂热,如今是又用这花为依据,将女人的偶像安置到心上了。”于是情不自禁,轻轻唱出情歌来。后来,吴姓兄弟从和尚口中应证了弟弟的遐想,隐隐约约的知道这束野菊花很可能是甘性女子留下的,谣传那个被大水冲走的女子大概并没有死,只是藉此逃开吴姓族人的追杀。尽管这样,弟弟仍想入非非,无心思打鱼,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渔”的
狂欢节里,“篓中无一成绩”,“只得一束憔悴的花”。 沈从文不止一次的在他的作品中写到“野花野草”。“野草野花”,注入了沈从文特有的“崇高的理想”、“浓厚的感情”、“蓬蓬勃勃的力量”,当然也象征美,象征生命,象征爱情。弟弟对拾到的这束野菊花爱不释手,不仅仅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女人”,而是为了要得到某种超越和感悟。因为他爱的这个“女人”,很可能是他的“仇人”,是父亲临死时叮嘱“必杀”的人。可见弟弟的“遐想”,本身就超越了“仇杀”,恩怨,凸显出了他的境界和憧憬,或者说凸显出了他对于民族和历史的反省。这“一束
憔悴的花”,使我们看到了弟弟的追求、执著和信念,
同时也融入了沈从文对于“人”和“人性”,以及民族未来的思考。
2,美丽盒子中的野蛮灵魂
“过去一时代”,乌鸡河两族之间的“仇视”,“流血为乐”以及毁灭人性的“大战”,使人感到悲哀和惆怅。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不断创造奇迹,积淀精神,却又彼此厮杀,相互残害,千方百计地毁损自身。人是文明的推动者,也是世界灾难之源。人可歌可敬亦可怕可悲。吴姓兄弟代表了苗民性格的两种典型:哥哥强梁如虎如豹,粗犷豪侠,但残留着一些“野蛮习气”。弟弟有智慧,有性情,能唱歌,渴望爱情,富有诗人气质。这两种性格,沈从文都很欣赏。他曾经写过两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虎雏》和《龙朱》。《虎雏》(19xx年)里的虎雏,是个年仅十四岁的勤务兵,秀气中透着威风,眼睛大而灵活,面貌出众,乖巧得很,气派极大。小说中“我”要把他留在上海,让他读书,用最文明的方法试着来造就他。可他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杀了人,逃走了。“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小说中的“我”为造就虎雏的计划落空而遗憾,但对虎雏的野性却非常欣赏。这个欣赏,与“五四”时期对民族性的思考是相呼应的。陈独秀就曾经说过,我们民族中缺少“兽性”,太柔弱了。把我们民族中原始
的、野蛮的,甚至是所谓的“野性”引向健康、强壮的方向发展,这大概就是沈从文当
年的一个“遐想”。
《龙朱》(19xx年)里的龙朱,有财富,有智慧,有容貌,有美德,而且健如雄狮,能唱歌。因为他太完美了,他周围的女子不敢爱他,从而使龙朱陷入爱的孤独中。沈从文在小说中指出:一个民族首先需要的,不是至善至美的典范,而是鉴赏的能力,是仰望典范的勇气。沈从文本人很喜欢“虎雏”和“龙朱”这样的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就叫“龙朱”,小的就叫“虎雏”。《渔》中的哥哥,犹如“虎雏”;弟弟则颇像“龙朱”。
沈从文把他们写成孪生兄弟,突出了他对这两种性格的欣赏和赞美。
和尚在小说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佛门以慈悲为旨。和尚本该劝吴姓兄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非但不该存有报仇的念头,就连鱼、蛇也不该杀,应该珍惜它们的生命才是。可是小说中的和尚显然不是个“善”者。“这和尚身穿一身短僧服,大头阔肩,人虽老迈,精神勃勃,还正如小说上描画的有道高僧。”见这兄弟俩都有刀,
就问:
“是第七族子弟么?”
“那是ⅹⅹ先生的公子了。”
“ⅹⅹ先生是过去很久了。”
兄弟俩问:“师傅是同先父熟了。”
“是的。我们还??”
这和尚,想起了什么再不说话,他一面细细的端详月光下那兄弟的脸,一面沉没在一件记忆里。 他对弟弟的刀“赞不绝口,说真是宝刀。那弟弟把刀给他看,他拿刀在手,略一挥动,却便飕飕风生,寒光四溢。弟弟为之抚掌:“师傅大高明,大高明。”后来,和尚又隐隐约约谈到甘姓朝字辈的族人还有后人的事。既认识这兄弟俩的父亲,也知道他们的“仇人”。据此,我们可以猜测他的身世,大概原本也隶属“吴姓”这一“小族”。小说中对于和尚有二处评价,一处是作家沈从文说的:“和尚所知道太多,正象知道太多,所以成为和尚了。”一处是弟弟对和尚的评价:“他还说唱歌,那和尚年轻时可不知做了什么坏事,直到了这样一把年纪,出了家,还讲究这些事情!”如果说沈从文的评价是一种善意的警告:知道得太多——做得太多,只能忏悔。那么“弟弟”的评价就是对“罪孽”的厌恶。和尚的出现,使小说的历史感更加厚重,也为塑造这两兄弟作了铺垫。吴姓兄弟在“渔”这个“热闹”的时节,忙里偷闲,到山上的庙里访和尚,这个
情节,堪称这个短篇的点睛之笔。沈从文在《烛虚》中说:
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和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是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
“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更长久的时间。
兄弟俩上山到庙里访和尚,其实是让他们在狂欢来临之际“静”下来,在“静”里得到“知”和“慧”,彻悟“爱”和“怨”,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把生命和灵魂中失去的东西找回来,重新用一种“带胶性的观念”粘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生的我”(《烛虚》)。
这大概就是沈从文写兄弟俩寻访和尚的用心所在。
这个短篇风格也很别致。是小说,也是诗;是写实的,又富有浪漫情味和传奇的色彩;是野蛮的习俗,又凸显出一种强悍而荒诞的美;是悲剧,却又给人以美的遐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性和人生美好的一面。有仇必有爱,人类的心灵深处还有爱情。小说当然总是虚构的。在“渔”的节日里,弟弟捡到的那束花,未必真的就是甘姓女子留下来的。沈从文这么写是有双重的意义的,是在说明这甘姓女子也有期盼,不仅仅只是爱情。弟弟捡到这束花后唱的歌,其实就是对这
束花的解读:
你脸白心好的女人,
在梦中也莫忘记带一把花,
因为这世界,也有做梦的男子。
无端梦在一处时你可以把花给他。
柔软的风摩我的脸,
我象是站在天堂的门边——这时,
我等候你来开门,
不拘那一天我不嫌迟。
“我象是站在天堂的门边”,“等候你来开门”,这大概就是沈从文的“对人生远景凝眸”,是对于人、人情、人性的诗意的表述。两个有世仇的家族的后人在“天堂”相会,这美的憧憬、美的人性,与湘西“地极荒,人极蛮”的这片古老大地月色中迷人的、如梦如幻的山野景物融合在一起,更增添了小说的蛮荒
气息和感人的魅力。
沈从文曾经说过:“美丽总使人忧愁”(《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在某一姿态下,所谓人情的美的认识,全是酸辛,全是难于措置的纠葛。”(《灯》)我们可以从《渔》中体会到这种美的忧郁的气氛。《渔》中的残酷而糊里糊涂的仇杀、报仇,使沈从文对于“人”,对于“生命”产生了忧患意识。忧虑生命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会丢失。沈从文写这些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于“生的意义”的明悟。《渔》值得回味处颇多。沈从文写这个短篇,大概是希望我们知道一点“过去”,知道在湘西大地上曾经有过的“生死哀乐”;其次是引导我们知道“人”,人事中杂糅神性和魔性,人性中有美好的一面,也有残酷的愚昧的一面。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好地探讨生命的意义,懂得人生的一种方式是“爱”,要在有生中发现“美”。人要有一个健康雄健的人生观,要有博大坚实而富有生气的人格!这大概就是沈从文在这个短篇中对于“人性”的思考,也是这个短篇深层的意蕴。19xx年沈从文为萧乾《篱下集》写的
《题记》中说:
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 上打算计较,不拘泥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地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
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的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的事业伟大作品,就是这类人有份。他不能避免失败,他失败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即刻可以爬起。 沈从文自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行为和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泥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能硬起脊梁,笔直地走自己要走的道路。从《渔》中,尤其是从弟弟身上,我们似乎也能体会到这一点。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20xx年10月21日
-
沈从文名言录
今夜月色如洗我别无他话只想将沈从文送给月亮与你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
沈从文的名言
沈从文的名言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溪面…
-
沈从文名言录
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沈从文边城喜欢157加入句集评论1难得糊涂分享到微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
-
沈从文先生百年大师地位的确立
ZHCHJXCOMZJFXGSCOMSHIYAN98COMWHJARJCOM沈从文先生百年大师地位的确立日是沈从文百年诞辰经过一个…
-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浅谈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沈从文曾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
-
沈从文名言录
今夜月色如洗我别无他话只想将沈从文送给月亮与你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
论沈从文的《边城》
论沈从文的边城论文提纲在沈从文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边城在人物的塑造及审美艺术特色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沈从文…
-
沈从文的爱情
沈从文的爱情世界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在和追求长达四年之久的张兆和…
-
沈从文笔下的“人性”——以《萧萧》为例
我所理解的沈从文笔下的人性以萧萧为例华师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俞明海沈从文的以描写湘西原始民风的作品向来被赞誉为歌颂人性的至美表现人性美…
-
从爱迪生的名言说起
从爱迪生的名言说起齐鲁师范学院山东省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徐洁爱迪生有一句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非常令人不解的…
-
沈从文名言录
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沈从文边城喜欢157加入句集评论1难得糊涂分享到微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